【人間書訊】《人間思想》第20期:馬克思主義在東亞
在當下的「後冷戰時代」,「馬克思主義」常常可能成為被刻板印象化的標籤,對「東亞」的討論開展多年卻進展徐徐。在這樣的考慮之下,我們選取了四篇重「分析」少「判斷」的文章,並依照文章內容的時空順序排序。這樣的做法,希望能盡量避免過多的「定論」,不是去評斷「這是當時或當下的局限」,而是希望我們和讀者都能更多地去思考自身歷史及當前所在的位置,從中尋求前進的可能和保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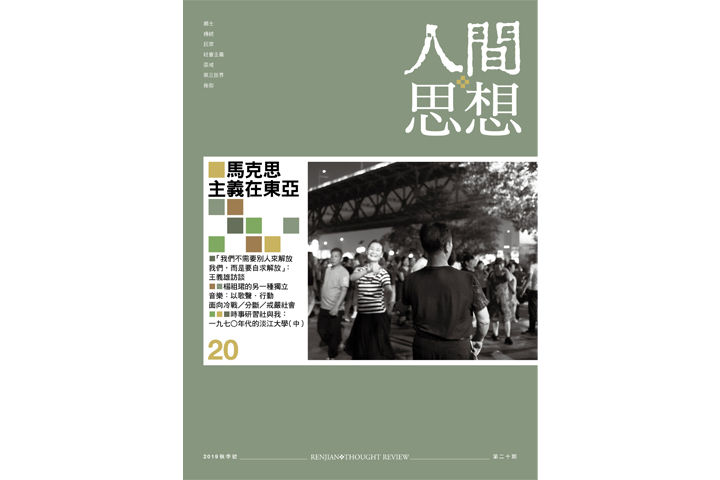
【編輯部編案】
重新連繫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是本刊自創立始訂立的自我期許之一,我們曾經組織了多期以「亞洲思想」為關鍵字的專號並集中推介過崔元植、曼達尼(Mahmood Mamdani)、板垣雄三等重要亞非地區思想家的著作。本次「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專號也是此知識計畫的延續。
在當下的「後冷戰時代」,「馬克思主義」常常可能成為被刻板印象化的標籤,對「東亞」的討論開展多年卻進展徐徐。在這樣的考慮之下,我們選取了四篇重「分析」少「判斷」的文章,並依照文章內容的時空順序排序。這樣的做法,希望能盡量避免過多的「定論」,不是去評斷「這是當時或當下的局限」,而是希望我們和讀者都能更多地去思考自身歷史及當前所在的位置,從中尋求前進的可能和保證。
冷戰體制不只造成歷史的忘卻,也剝奪了識別歷史遺產的視野和語言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跨語言、跨境的大田英昭和汪力二人的文章不僅是單純的文本生產,也應該視為超克冷戰主體的知識實踐。中文世界中少有「社會主義」概念在日本傳播與展開的整理性檢視,大田英昭的文章對這個過程進行了清晰細緻的分析,有心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如能參照自身歷史做歷時性或共時性的思考和反省,相信會受益匪淺。而汪力對尾崎秀實在中日戰爭前夜評論的細讀和梳理,可以幫助我們不僅對尾崎、也對中日戰爭有更加立體的理解。
專號的後兩篇是以台灣為中心的討論,但談論的絕不止於台灣內部。陳柏謙的文章本身就是極重要的歷史材料,作者長期投身於對1950年代台灣工人運動的研究和口訪工作,此次的文章是其多年積累的階段性成果。李清潭的文章涉及當下的全球焦點「中美貿易戰」,而此文做於一年之前,多少可見其「先見」,作者通過歷史事件和理論方法層層推進的書寫方式,也對文章的易讀性和可讀性加成不少。
最後必須說明及感謝的是,本次專號文章都來自去年(2018年)11月17-18日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辦的第一屆「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術研討會,除了謝謝四位作者的慷慨賜稿,還要特別感謝承辦單位華東師範大學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所所長呂新雨教授、常務副所長林哲元副教授對本刊物的信任和鼎力協助。
【目錄】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十一):以陳映真為線索】
004 「我們不需要別人來解放我們,而是要自求解放」:王義雄訪談 林麗雲、陳瑞樺 主訪|郭佳、呂怡婷 整理
047 人生有芳華:側記王義雄/林麗雲
【專號:馬克思主義在東亞】
050 編案/編輯部
052 「社會主義」概念在日本的傳播與展開/大田英昭 069 尾崎秀實論中日全面戰爭前夜的東亞局勢(1934.10-1937.6)/汪力
109 舊台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1945-1950)/陳柏謙
154 《台灣關係法》、美台軍售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治理的新模式與新殖民主義的商品化/李清潭
【視覺筆記】
199 江城漫遊漫記/曾笑盈
203 影像選輯|武漢之對視/曾笑盈|文.攝影
【異議】
211 楊祖珺的另一種獨立音樂:以歌聲.行動面向冷戰/分斷/戒嚴社會/劉雅芳
【當代史】
242 時事研習社與我:一九七○年代的淡江大學(中)/龍紹瑞
275 作者簡介
277 《人間思想》稿約
278 《人間思想》書訊
《人間思想》第20期【試讀篇章之三】
楊祖珺的另一種獨立音樂:以歌聲.行動面向冷戰/分斷/戒嚴社會
文:劉雅芳
祖珺印象
第一次知道楊祖珺(1955-)的名字是在張釗維的探論1970年代現代民歌發展史《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1994)書裡,當時我還在台北讀大學。真正見到她的人是在2003年一場由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林孝信所主持的「音樂運動!社會運動!」座談會,她是與談人之一。至今,我仍記得當她說起「以前」所經歷的事情時,突然之間忍不住哽咽暫時走出座談現場的場景。往後楊祖珺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大致上就是與「民歌運動」、「社會運動」等詞彙緊密相連(即使當時我仍未聽過〈美麗島〉與〈少年中國〉的任何一個版本錄音),但我並不那麼有機會繼續深入瞭解她所經歷的時代與哽住氣息的情感情緒,即使2003年她那突然起身的畫面一直在我的腦中留下清晰的記憶。
當時的我身處在九○年代以來的本土化運動熱潮延續至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氛圍裡,只知「解嚴後」、「狂飆的八○年代」,對「戒嚴」、「黨外運動」並無超過大學通識歷史課程所傳授的一般認知。「左派」是隨著社會科學課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內容浮現的符號,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在地內容的指涉,以及後來知道的「左翼」與統獨、省籍、國家/民族主義等盤根錯節的糾葛。
往後在2008年《關不住的歌聲:楊祖珺1977-2003錄音選輯》出版之際,「再.見美麗島:楊祖珺全島發聲」系列座談於新竹清華大學人社院的場次,我才再有機會見到楊祖珺並現場聽到她彈著吉他講唱歌曲的創作、演唱背景與歷史。當時的我已經因為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蒐集夏潮聯合會統籌企劃、黑名單工作室王明輝擔任音樂總監的《七月一日生》(1997)合輯時,聽過她與胡德夫合唱最早錄音版本的〈少年中國〉(1977)。那時,我依舊記得2003年的印象,仍無法開口探詢,即使她對待我輩年輕人們如此親切和藹。然而她又讓我留下了另一次印象,這次是充滿歌聲的。
她在清大人社院的演講廳裡,彈著吉他調音,之後循著從七○年代淡江校園傳遞出來的「新民歌」:〈我知道〉、〈美麗島〉、〈少年中國〉等歌曲唱起來、講起來,帶著我們走進歌聲與她所經歷的歷史現場。但是我卻是在初次聽到的她所創作的〈累了嗎?〉歌聲當中,感覺到了通俗音樂作為一種情感文本,為個人的身心疲累狀態所帶來非常直接的安慰──一種彷彿只有這首歌是她來唱、你聽到了才可以成立的瞭解。我在如是的演唱步驟中,隱隱的感受到她先讓自己是一位傳唱者民歌手,才是一位女性創作歌手(即使當今不管流行或獨立音樂,「個人創作」這個標籤多麼的需要彰顯)。
之後,我陸續在「保釣國際論壇」(2009)、文化研究相關的場合(最多是與公眾較接近的台北清大月涵堂)、南藝大、思想性研討會,陸陸續續再見到她的身影。近幾年在交工樂隊「《我等就來唱山歌》發行十五週年紀念演唱會」(2014),聽見她擔任嘉賓演唱心靈版〈美麗島〉。也遇見她安靜的坐在舉辦日日春麗君阿姨追思晚會(2014)的公園階梯,在白色恐怖受難者紀錄電影《東所》(2015)於前軍法處青島東路封街露天放映現場,以及在黑手那卡西告別演唱會(2016)作一名認真隨著音樂歌聲而喜怒哀樂的聽眾。
這一路以來,我也因為學習、工作的緣故,並不特意的知道了她從一名喜歡唱西洋歌曲的學生歌手,成為一名推廣「唱自己的歌」運動的民歌手,到身為參與黨外運動、創(合)辦黨外雜誌的推動者,一位母親,以及常常現身社運場合的大學教授等歷程。但是,2003年初見她的畫面依舊沒有淡去,〈累了嗎〉的歌聲始終令人不知不覺的想起。這時我已比十多年前更知道些,原來從七○年代「唱自己的歌」以來,她所經歷的並不是我概念式地知道「戒嚴」、「解嚴」的歷史過程而已。是以她的生命與聲音去提問、關心、抗爭所照見的歷史,那些被主流社會價值所壓抑的主體、並不輕易被看見者的歷史。從1978年為了松山廣慈婦職所受害雛妓少女所籌辦的「青草地演唱會」開始、黨外運動、關注白色恐怖受難人、外省人老兵返鄉運動……聲援楊儒門及台灣農民/農業行動、保留樂生療養院運動、支持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等等。當有了這個體會,我有時認為,會忘不了2003年她那一個暫時轉身的畫面,是因為她把照見的那些歷史變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也許太重了,以致於誰也無法代替誰的「一言語之」。幸而當她彈起吉他、唱起那些跟著一起走過歷史現場的歌曲是有力的、澎湃的。
以此,可以看到楊祖珺以民歌手的身份出發所捲動的社會歷史系譜是繁複的,且承載至今。當前多數人見到她時,多還是以七○年代活動至今的民歌手為主要印象,且累積的認識多是「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形象。在歌唱上不喜歡彰顯個人,且自居為李雙澤的歌傳唱者的她,卻是打從1973年聯考放榜後開始學吉他、唱美國民謠以來就有許多對音樂和製作的想法,卻少有人討論。本文將以1970年代至今,楊祖珺所唱的歌、參與製作的專輯為線索,試以勾勒她的音樂和思想、社會行動的關聯。這也是她從一位彈著吉他在校園、民歌西餐廳、民謠民歌演唱會唱歌的民歌手,到推動「唱自己的歌」運動,至黨外運動時期手持「大聲公」在街頭運動、選舉、抗爭等現場發表意見、抗議,也還是唱歌,再到近二十年為了需要她的歌聲的社會運動而歌唱的歷程。
一、雖然沒有成為那樣的瓊.貝茲(JoanBaez):唱「自己的歌」走進社會生活的異境
1973年10月14日
平淡的事物往往較濃烈來得持久。一些簡單的敘事歌給我很大的衝擊。像JoanBaez自彈自唱的〈DonnaDonna〉:小牛是這麼容易被人捉綁、屠殺/牠們卻從不知道為了什麼/誰叫你們沒有燕子的翅膀/自由驕傲地在天空飛翔……/不祇是旋律,甚至這些歌詞都深深教育了我,我願意做這樣一個歌手!
──楊祖珺,1979年
有一個小孩他今天誕生了/有一個小孩他今天誕生了
從今天起我們要關心他/從今天起我們要鍛鍊他
在風雨中他並不懼怕/在陽光下他勇往直前
在挫折時他並不灰心/在快樂時他與人分享
等到一天這個小孩長大了/他能將眼淚化為歡笑
他能將懦弱化為堅強/他能將憎恨化為愛心
有一個小孩他今天誕生了/有一個小孩他今天誕生了
──〈誕生〉(1979),詞曲、演唱:楊祖珺
如果1970年代年輕人唱自己寫的歌以楊弦「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1975年6月6日)為檯面上的開端,那麼隔年李雙澤於淡江校園「民謠演唱會」(1976年12月3日)上的登高一呼「唱自己的歌」則是試圖對創作民歌、唱民歌建議另一種方向。李雙澤的建議方式雖然如突來行動劇般帶來了衝擊性,但也不能不說是蓄積了許久的思考與觀察,在肯定前人、同代人已努力的前提下覺得還可以再推進。楊祖珺即是當初在同個舞台上的另一位演唱歌手,她那天唱的是瓊.貝茲的歌曲。當時她還是淡江英文系的學生,她也受到了李雙澤行動的衝擊,且在當時才認識的同系王津平老師鼓勵下,寫了一篇回應的文章,參與了當時《淡江週刊》幾波針對「李雙澤事件」所引發的「洋奴心態」、「為什麼不唱中國歌」的討論。她在文中提到:
人都是有自尊心有民族性的,我相信沒有一個人當他手持吉他口唱洋文時,心中會得意洋洋地想:「這就是代表我民族的歌」。……
我們與其問:「中國人為什麼不唱中國歌?」不如自問:「中國人怎麼唱不出中國歌?」誠然,中國的民謠多得不勝枚舉,然而大多數的歌曲,搬指算來都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身為接棒人的這一代,尚不能延續其命脈,卻在那兒跟著別人搖旗吶喊,口誅筆伐的大吼:「中國人為什麼不唱中國歌?」我們不妨自忖:「我可曾貢獻出一滴點的心力出來,讓中國人有現代的中國民謠唱呢?」古老中國民謠的旋律確實迷人;但一昧沉醉於美好的回憶中,我們不嫌自己太不負責任了嗎?
李雙澤便是看了楊祖珺的回應與挑戰後受刺激,更著手於創作「新歌」。之後,楊祖珺開始跟「以前」不太一樣,開始唱起台語歌謠。然而,此時楊祖珺的心中已對年輕人喜愛的美國1960年代已降的民謠有了屬於自己的看法。如同她挑戰李雙澤的文章,我認為她指出的即是一個「中國」民謠如何找到一個現代的表現方式的問題。這個「現代」的表現方式不僅是針對音樂上、樂器上的,還包括內容,以及聲音如何詮釋。她在第一張專輯出版之際即提出「生活、音樂、文學與思想」四個要素,想與創作歌謠的同道們共同勉勵。這四個要素簡要的在李雙澤身後,持續呼應他倡議「唱自己的歌」的精神。楊祖珺在規畫、製作第一張專輯時即試圖面對以上的問題。
在進入分析楊祖珺的第一張專輯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她此時對音樂的想法,以及以民歌手走進社會的場景,亦象徵把淡江-《夏潮》文藝路線所推進的「唱自己的歌」與作品從校園文藝運動範圍帶入社會面對民眾。我們可以從她當時的自述裡,察覺到當她開始理解到美國來的「流行音樂」當中,「folksong」(尤其是瓊.貝茲的歌)裡不太一樣的內容時的轉折:
在高中階段迷戀搖滾音樂的時候,我最受不了JoanBaez的歌聲,那時的我總覺得她那麼死板的唱腔憑什麼風靡了美國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但慢慢地,我注意到某些歌曲的歌詞,訝異地發覺,其中所包涵的東西,是那麼地合乎人道,那麼地洋溢著對人類的愛,而這些歌曲,絕對不是那些一味發抒男女間情感的歌曲所能比的。就這樣,我轉而對PeteSeeger、BobDylan、JoanBaez熱愛起來,也同時因為喜愛和了解這些歌曲,我認識了李雙澤。
和許多台灣戰後年輕一代一樣,楊祖珺也是從喜歡美國流行音樂後,開始由聲音/音樂上的喜好轉而對內容的理解。李雙澤為她帶來的反思契機則是可以從「中國」內部的傳統去找音樂與歌的資源。一面從施庇德(PeteSeeger)的思考中理解到:「當音樂本身與人類生活戚戚相關、血肉相連時,便是最好的音樂。」她認為要在音樂的天地裡落實對社會人群的「愛心」,若藝術工作脫離「同胞的生存與生活」便會陷入「模仿的或空洞的困境」。一面從瓊.貝茲學習吉他,成為百萬唱片民歌手「歌星」到政治參與,由反種族歧視、非戰、非暴力主張者成為反戰的行動者之歷程理解到「祇有聲音是不能表達音樂的」。她注意到瓊.貝茲的歌曲敘事中「喜歡用歷史事件中的細節來印證今日的事實」,像是要傳達反越戰的訊息,卻是用回憶的方式敘述美國南北戰爭帶來的民眾苦難,在關注越戰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同時間巴基斯坦的內戰並寫了首歌。
楊祖珺當時參照施庇德以及瓊.貝茲的創作社會背景與想法,所呼之欲出的是,創作歌謠可以開創關心社會與生活的內容,而此「社會、生活」若由同時代美國民歌反戰的內容連結出去,並不限於國境之內。也是在這個層次上,她所體認到的美國六○年代以降的民歌,除了是在面對美國內外的社會現實、問題而傳達的思想,它們更是一種與他者或同道溝通和了解的方法。有別於瓊.貝茲等人是在自己的社會裡創作、試煉音樂的操演和內容,李雙澤、楊祖珺明顯地在美國戰後於亞洲的文化冷戰支配基礎下,接受到這一波有社會意識內容的青年音樂文化,在七○年代台灣的歷史、文化、社會意識復甦的潮流下,自覺於要在「兩個世界」中尋找新的出路。楊祖珺的實踐方式之一,即是在李雙澤過世後,持續唱他的「新歌」,讓這無法進入當時唱片生產與傳播機制的歌曲,在社會中仍有被傳唱、聽見的機會。對楊祖珺來說這也是透過唱歌,面對社會、尋找社會的方式。
在1977年9月楊祖珺大學畢業並以「唱自己的歌」作為運動的職志,到1979年4月新格唱片推出她個人專輯期間,她參與了不少事情。在音樂上,她持續尋找自己文化中的音樂傳統──「中國的調性」,學習蘇州彈詞與北方大鼓,以及在台灣現地場景裡訪查民間音樂、傳統音樂,如:公園裡的老人賽歌、歌仔戲演變的歷史。在這段時間,她也是年終排行榜上,中國現代民歌票選中,最受歡迎歌手之一。她所唱的他人寫的民歌,如:〈思鄉人〉、〈三月思〉、〈鄉愁〉等,時常登上電台民歌排行的前十名。也受邀擔任台視「跳躍的音符」民謠節目主持人,最後因不滿新聞局要求其演唱「淨化愛國歌曲」而辭職。當時她並不抗拒偏向主流的媒體與傳播方式,是因為認為那也是推廣李雙澤的歌以及繼續推動「唱自己的歌」的機會。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她的籌劃之下,於台北市榮星花園舉行「青草地歌謠慈善演唱會」(1978年8月16日),是為廣慈博愛院婦女職業訓練所的雛妓少女募款,也是召集了當時青年民歌手的集體戶外售票募款演唱會。這段時間,除了仍活躍於民歌演唱的場合,也參與《夏潮》舉辦的民歌座談,以及有不少報導文字發表於黨外雜誌的她,還應王拓參選基隆市國大代表之邀為「黨外」助選,在競選活動中安排音樂演唱節目。同樣是以歌手的身分接觸社會的行動,青草地演唱會慈善行動的面向得到當時兩大報與大眾傳媒的肯定,警方更主動表示可以幫忙維持現場秩序。但是演唱會的社會性與關懷底層的面向,卻受到當局以「串連工運、學運與社會運動」的目光檢視,日後又以她與「黨外」政治沾上邊為理由,逐次封殺她到學校和工廠演唱,僅剩下到社會團體、慈善團體的演唱機會。查禁所及,她的唱片發行不到兩個月遭回收。她以唱〈美麗島〉、〈少年中國〉作為起始元年(1977)的「唱自己的歌」運動也走向七○年代的尾聲,繼之轉向八○年代「後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脈絡。
如果以「唱片論」來看,楊祖珺嚴格來說並不是典型以出唱片起家的歌手,也不以個人經典化的專輯唱片定義其為歌手的本色與才藝。她當時是少數「橫跨『中國現代民歌』及淡江-《夏潮》兩條路線」的歌手,策畫的演唱會也多能招攬當時已頗有名氣的民歌手參加,演唱會的曲目安排也是打破歌手唱自己招牌歌的模式,是依照隨演出場地、聽眾而設計的曲目。演唱會的最後一定有台上歌手與台下觀眾大合唱的安排,多是以唱李雙澤、梁景峯所合作的歌曲為主。她的第一張專輯出版後不久回收,以及政治封殺日緊,唱片內容與音樂表現如何並不來得及接受當時大眾媒體與通俗樂評的評價,繼之唱片的傳播路徑也轉為地下。因此,唱歌作為表演或理念的傳播在她身上,是以現場、面對群眾作為主要的依據。張釗維曾論及如此的傳播管道固然由結構性的社會因素造成,但楊祖珺與淡江-《夏潮》路線所代表的偏向左翼關懷的與現實主義的表現,卻也缺乏發展「建構一套關於音樂形式和其相應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機制」,因此無法發掘與再生產更多的新歌手與新作品。與此同時,相對主流化的「中國現代民歌」路線與其再生產機制「金韻獎」(1977-1984)和製作發行現代民歌、校園民歌的唱片公司越來越多,直待羅大佑推出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1982)才再掀起一波遍及流行音樂、文藝場域的對於搖滾樂、通俗音樂的表演形式與社會意識內容的討論。
多年後,楊祖珺雖然對於自己的第一張唱片表現表示並不滿意,覺得自己「不在狀態」,她提到:「其中矯揉造作的歌聲,是我當時被歌唱技巧驚嚇到而自以為是的呈現」。錄製這張唱片到出版花了十個月的時間,她邀請張照堂攝影與設計封面、蔣勳寫「序」,她自己也寫了回憶札記。在音樂製作上邀請當時剛出道不久的陳揚擔任編曲,歌曲的樂器編制上有新格管弦樂團的伴奏,搖滾樂的配器吉他、貝斯、鼓、電子鍵盤,細聽還有傳統樂器南北管的樂器配置。在錄製歌曲方面,她本來答應新格出唱片的條件之一即是錄製李雙澤所參與創作的歌曲為主,但是歌曲送審的結果出來,只有〈美麗島〉通過可以錄製在唱片但不能在廣播電視播放的規定。最後錄製完成的曲目,一面為創作曲,一面為傳統民謠,當中有兩首楊祖珺的創作歌曲:〈誕生〉、〈我唱歌給你聽〉;「時代歌謠」之〈農夫歌〉(詞:黃仲樵;曲:陳揚);民歌手朱介英的作品:〈風鈴〉、〈金縷鞋〉;〈美麗島〉以及台灣與中國大陸各地民謠。
當時,這樣將新歌、傳統民謠放在同一張唱片的製作方式,並不少見。然而,這張專輯卻是〈美麗島〉(也是李雙澤的歌)第一個由商業唱片公司出版正式錄音的版本。楊祖珺的新歌〈誕生〉以小孩、新生命為敘述主題,充滿對生命的熱情和理想,也頗有李雙澤與梁景峯〈我知道〉中與小朋友(新生)對話的精神,尤其是歌詞那一句:「他能將憎恨化為愛心」,也是當時許多青年關心社會的寫照。〈我唱歌給你聽〉則精神與〈老鼓手〉(詞:梁景峯;曲:李雙澤)、〈我們都是歌手〉(詞:林華洲;曲:梁景峯)一致,傳達了「大合唱」、「一起唱歌」的渴望:「讓我們一起來唱歌/不要站在一旁/讓我們一起來歌唱/歌唱出熱情和希望/歌唱出理想和主張/像花兒遍地的開放/像蝴蝶四處的飛翔」。值得注意的是,這張專輯中的〈農夫歌〉是《夏潮》在1978年6月刊所設立的「時代歌謠創作獎」,所徵選到的「工作歌」歌詞。這首「新歌」應是這一波徵選作品裡唯一有錄製成為唱片曲目的,也留下了《夏潮》集團當時想繼續延續李雙澤等人淡江民歌路線的足跡。
在音樂的呈現上,楊祖珺雖然後來不滿意,但是在這張專輯中她的歌聲與她錄製收於《我們的歌:中國創作民歌系列》1-3集(1977-1978)的歌曲〈三月思〉(詞曲:朱介英)、〈媽媽的愛心〉(詞曲:吳統雄)相比,已與委婉平述的歌聲表現有所差別。在1979年的專輯中,她自己的歌唱起來清新明亮,其他歌中,有時試圖吶喊、有時試圖俏皮,歌聲的轉折有時呈現出刻意不那麼「輕」的力量,雖然與她近來的歌聲表現相比差異很大,但也像是還在摸索自己聲音的「個性」。在編曲中,〈農夫歌〉最能突顯她當時內心與外在世界遭遇變化與挑戰的特質。這首歌其古樸甚至略顯故作鄉土氣息的歌詞,搭配的卻是大量的民間傳統樂器南北管、西洋電子合成器、貝斯、電吉他和弦樂的編制,以西洋電子鍵盤重複的和弦貫穿著整首歌做為襯底,電吉他與貝斯的彈奏節奏使得這首歌的音樂展現了「放客」(Funk)與搖滾的色彩。楊祖珺在這首歌的唱腔則是以傳統民謠加民間小調的方式來演唱。此首歌的編曲跟同時期民歌編曲的木吉他民謠風、輕淡管弦樂風相比,是比較「電」的,而且比較創新的,但嚴格來說並不是一首「搖滾樂」歌曲。透露了當時通俗音樂的製作與生產,在音樂與節奏上使用樂器、適應西方最流行的節奏等技藝表現並不是問題,搭配傳統樂器「jam」也不太是問題,出現「不適」、矛盾的是歌詞內容與音樂表現的搭配上透露的舊/新時代差距。那是不是也是當時青年知識份子(包括尋索左翼脈動的)重新尋找「鄉土」、自己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面貌時,所遭遇的銜接困境?以及一種處於現代社會下,重新面對「鄉土」與「傳統」時所面臨的「心靈」差距?因為所熟悉的「現代」語彙與方法,大部分都是西方的(美國的)。以致於難免必須拿「東」拿「西」的操練一番。這也是當時的青年以「民歌」(主要是以美國民歌作為形式與思維的引導)為介面來詮釋自己體會的「現代」時所展露的無法平整的痕跡。
但是,可以發現七○年代中期延續至八○年代的現代民歌、校園民歌,除了主催是青年的新創作(國語)歌謠之外,傳統的民謠也是其採用的基礎。此時這些被採用的傳統民歌、民謠並不那麼區分是大陸(中國)的或台灣的(凡以省分或縣市區域標示),只是採用的台灣民謠(閩南語歌)有時專輯上會以「鄉土」標榜,而唱傳統裡自己的民謠也是這一波民歌風潮的正當性和各方的公約數。再看當時的檢查機制不准楊祖珺錄製的李雙澤新歌,仔細去分析歌詞,幾乎每首歌的詞義都還不及當時許多青年熟知的BobDylan、JoanBaez等人歌曲的寫實性與批判尺度,更不及英美搖滾樂裡如Beatles等的叛逆或異議。唯其所採用的詩作、自寫的歌詞與當時還尚在起步的民歌創作歌詞相比,較不限於現代主義式的個人意境裡,是直白地提及農民、工人、漁民等青年學生之外主體的,更有唱及「窮苦的歲月」(〈我們都是歌手〉)。這些歌曲的精神與當時日趨成熟的鄉土文學的質地是更相應的,尤其提到勞動者與反帝反殖民(〈紅毛城〉)的面向。然而以當時現代詩論戰(1972)後,抵抗現代主義潮流的新詩作品開始出現,王拓、黃春明、楊直矗等人的小說開始有發表空間且日漸受注目,以及《夏潮》、《仙人掌》、《雄獅美術》等雜誌也出現報導文學、報導攝影的藝文生產狀態來看(且有不少年輕讀者與追隨者)。當時青年人的心靈表現,是更有空間創造出比李雙澤的歌更具社會現實關懷歌曲的。在李雙澤、梁景峯等人創作,楊祖珺想接著唱以介入大眾文化層次的這一組歌當中,可以感受到她/他們想將在地的(他們也參與其中的)文藝運動中的作品轉化為「民歌」之思想資源的強烈意圖。但是在當時歌曲的傳播,除非自己寫、自己小範圍的唱,要讓大眾聽見與產生聽覺的影響力卻必須先受當時審查制度的檢查才能有限度的傳播與出版。這反映了當時通俗音樂出版的審查機制「去政治化」的邏輯──反共=反工農兵意識=防止左翼,英文歌那樣唱卻不打緊,而唱片工業的商業本體也內化了這個再生產邏輯。而楊祖珺是在推動「唱自己的歌」運動、接觸黨外運動,以及想唱的歌的性質觸犯了當時「去政治化」的底線。
進入八○年代之後,楊祖珺幾乎與當時日趨成熟的通俗音樂界、唱片圈,大眾媒體中與流行音樂相關的管道無所關連。此時她的主要行動陣地轉移到黨外,唱片公司不能錄製的歌,她以自製募款錄音帶在黨外政治活動的網絡中販售與傳播。在這些黨外錄音帶中,我們可以發現延續了1979年專輯中,有傳統民謠與新歌的配置,以及持續傳唱李雙澤等人合作的歌。那一首曾經刻錄在黑膠唱片於1979年流通不到兩個月的〈美麗島〉,在八○年代將以黨外卡式錄音帶為傳播管道之一。這一道黨外歌聲的脈絡,將在下節進行討論。
二、黨外運動.街頭「搖滾」之聲與一百元黨外錄音帶:《黨外的聲音與新生的歌謠》(1981)、《壓不扁的玫瑰》(1983)、《大地是我的母親》(1985)
三十年!三十年不是短短的時間,三十年可以乎一個囝仔長大成年,也可以乎一個三十歲的人,變做一個六十歲的老人。
三十年的隔離,按台灣去看中國,看見中國在歷史的煙霧中,又擱生疏,又擱遙遠。中國啊!你何時才會平安,你何時才會勇健。何時啊!到何時,你才會享受自由、民主和幸福?
總是,少年的朋友啊,咱不要再流無用的目屎、無用再流浪,咱、咱是少年青春的中國,用咱的雙手,咱也可以創造一個民主、自由和幸福的中國。
──陳映真,〈少年中國〉口白文字,1981年
我要自然/草原青青/大地是我的母親
不要摧殘/美麗寶島/莫讓山河凋零
不要破壞/美麗寶島/好讓自然去成長
不要污染/清清流水/莫讓生命枯萎
不要破壞/美麗寶島/她是我們祖先開墾的河山
不要破壞/美麗寶島/她是我們孩子的將來
──〈大地是我的母親〉,1985年,詞:楊祖珺;
曲:FrankFarian&DavideSgarbi
進入八○年代,楊祖珺的生活與社會行動參與的主要陣地在於黨外政治與黨外聯盟推動的社會議題和社會、民主運動裡頭。此時的她也越來越脫離剛從大學畢業後仍繼續推動「唱自己的歌」的學生歌手形象,之後更走進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結婚且成為母親。這十年間,由於前一階段也曾參與到基隆黨外助選,以及與左翼文藝脈絡的認識,加上前夫林正杰是當時黨外運動的健將,因此以左翼-黨外為軸線,她拓展了與前一階段不同的歷史與政治相關的社會運動。由於牽涉的層面太廣,本節仍是以歌曲為軸線,尤其是她擔任籌劃製作的三捲黨外募款錄音帶:《黨外的聲音與新生的歌謠》(1981)、《壓不扁的玫瑰》(1983)、《大地是我的母親》(1985)談起,有限地討論她在八○年代的社會運動狂飆與政治風雲中仍未放棄的文化運動──以唱歌、做歌面對社會,以及在這當中她曾經產生退縮,不敢面對音樂的心情。與此同時,她亦從綠島出獄回來的「老同學」(白色恐怖政治犯)身上,學得了另一種民歌,以及在外省人返鄉運動中到北京開了民歌演唱會。
1981年起由於先前持續的政治封殺,楊祖珺推動的「唱自己的歌」運動,除了機會限縮,她也早已比較少參與當時正在熱潮上的民歌演唱活動。除了該年4月受新加坡文化部之邀,和吳楚楚一起參加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民歌手共同聯合演出的「四月風詩樂民謠演唱會」(1981年4月17-18日)。雖然該行主要目的是為星國的「華文教育」打氣,但也能看到台灣的現代民歌運動對周邊華人華文社會的影響。1980至1990年代的新加坡興起一波「新謠」(新加坡青年創作歌謠)運動,這些青年歌者也是在思索「自己/我們的歌」在哪裡的問題。
同年底,她受黨外「民主、制衡、進步」連線的台北市議員候選人之一林正杰之邀,錄製《黨外的聲音與新生的歌謠》(1981)以助選。這張專輯延續她以講、唱民歌傳遞訊息的精神,特別是邀請了作家陳映真撰寫每一首歌的引言口白。這些分別以國台語讀出的口白以及台灣民謠、國語新創作歌謠的相互搭配,猶如一捲以「當代」歌聲串起的台灣-中國近現代史略影。彼時尚處於戒嚴,國語和台語(閩南語)尚仍有強烈的官方與民間之對峙性存在,以及與之派生的省籍情結。這張專輯反映她「關心政治的想法」,以及「表達各語群的融合」,她提到:
我設定「黨外的聲音與新生的歌謠」為主題,在和小說家陳映真溝通了一下午之後,他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在每首歌曲之間描寫口白。我的想法,是用台語民謠來簡介台灣歷史,用創作歌謠來描述我的理想。而口白使用的語言,用國語介紹台語歌、用台語介紹國語創作歌謠,用以表達各語群的融合。「黨外的聲音」放在A面,「新生的歌謠」放在B面。
這張專輯在錄製後,「新生的歌謠」部分由於同一陣線的其他候選人覺得「外省味」太重而沒有採用。然而,這一面的七首歌中有四首是李雙澤等人的創作歌曲:〈愚公移山〉、〈我知道〉、〈少年中國〉、〈美麗島〉。整張專輯,她並沒有採用自己的創作。
在這一、兩年之間,現代民歌因為種種檢查機制的限制與商業出版量化的問題,越來越走向「校園民歌」化。然而,羅大佑於1982年推出《之乎者也》專輯,其不論歌詞內容與音樂表現,都更明顯地超越同時代的流行「校園民歌」,尤其是歌詞現實性與人文關懷的厚度。楊祖珺在1983年參選立委的自製專輯《壓不扁的玫瑰》(1983)即採用了兩首羅大佑的歌:〈之乎者也〉(1982;楊改編詞為〈台灣之乎者也〉〔1983〕)、〈亞細亞的孤兒〉(1983)。楊祖珺此時雖已遠離大眾媒體網絡的「歌唱界」,但仍持續關注民歌的發展。亦曾發表專文探討現代民歌持續發展到八○年代的一些變化,首先她以1978年3月後新格唱片開辦金韻獎為界,將民歌的發展區分為前後階段。她認為金韻獎開始後的民歌創作,出現前一階段所沒有的「年輕人『疏離』心態」,這固然與前述已提及的檢查機制問題有關。但是她也發現「民歌」開始量產後,年輕人一方面少了從西洋民歌中去琢磨「成熟的思考性歌詞」,一方面也少了前一階段強調「多做歌」的精神:
我要說的,並不是聽民歌是好是壞的價值問題,而是民歌減少了年輕人聆聽音樂的豐富性。在作曲者絕大部分都是「靈感創作」,編曲者也局限在五、六個編曲熟手裡。作為管道的商業集團都礙於「規定」而自我約束,審核音樂之有關機關之改革的力量,又無法突破老成的上一代,年輕人祇聽民歌,反而有違了民歌創始的意義。
楊祖珺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反思民歌當時遇到的發展困境,以及鼓勵學習當時羅大佑所突破的創作型態。這也反映民歌發展在彼時已經呈現單調化,喪失文化運動的精神。
1983年3月14日,楊祖珺籌辦且命名的《前進》(Progress)週刊創刊。這雖為黨外政論性刊物,但是楊祖珺擔任「一人編譯室主任」、開闢撰寫「外國月亮」專欄以介紹世界大事和進步社會思潮,引介當時台灣主流思維之外的國際新聞報導,亦包含第三世界的時事。《前進》不只報導政論,還關注民歌、電影等文化議題,以及白色恐怖受難者議題和大陸的新聞(「大陸半月記」專欄)等等。然而,在如此忙碌於刊務和協助林正杰的事務狀態下,她在一陣自我決定與歷經波折後,以黨外人士的身分參選台北市的立法委員(1983年9月)。這次參選受到文化界人士、「統派」,以及《夏潮》和《前進》系友人的幫忙,楊逵與羅大佑更到場站台。她這次的選舉即是有所意識地選用了抗日作家楊逵的文章〈壓不扁的玫瑰〉作為競選的主題,為了募款更錄製同名專輯與編著同名專書集結個人評論和羅大佑、吳祥輝等人文章。她的競選理由裡提出:「抗議人吃人!愛每一個人!這就是壓不扁的玫瑰!」
這次的選舉結果雖然楊祖珺沒有當選,但是每一場政見演講以分送民眾玫瑰和歌聲結束,營造了不同的選舉氣氛,像是「演唱會」一般。且在當時二二八、白色恐怖、政治犯、海外黑名單、省籍、返鄉探親等問題仍屬禁忌的狀態下,楊祖珺的政見發表仍提及這些歷史問題。因此,她的政治參選也融入了文化和歷史運動的生氣,政見更融入她非常重視的性別平等與環保議題。她於每場政見發表會都唱四首歌,也舉辦「民主、民謠、抗議歌曲演唱會」,提出:「在歌聲中前進」。當時的情況如下:
民國七十二年,我自己成為候選人了。為了完美而適切表達音樂的完整性,我將分期付款尚未繳清的山葉鋼琴,在每場政見發表會中搬來挪去,不論颳風下雨;而胡德夫、王永、鄭盈湧也在每場政見會上和我一齊出現,好像又回到了從前!
大致從1982年8月,楊祖珺暫停於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亞洲研究所學業回台後,她就整個投入黨外政治活動的網絡。無論是當時林正杰的,或是她自己所關注的黨外與社會運動網絡。此時期,她的歌聲、吉他,除了展現在自製的黨外錄音帶,多是在街頭運動、選舉政見發表會、與黨外和《夏潮》系網絡有關的紀念活動或集會裡頭。在黨外運動時期,以販售書刊雜誌、錄音帶來募款,是很常見的募集資金的方式,而且多半是民眾在你面前把現金直接交給你。這種以文化物件募款的方式,一方面是因應當時仍有出版和言論管制,而這些物件也是串連彼時關注主流媒體報導之外社會現實的人們的方式。突顯當時黨外打的民主運動、選戰,是政治的但是嚴格來說也是文化的。楊祖珺在這一脈網絡中,她的聲音時常伴隨著固定場合的講台麥克風,或街頭、臨時集會場合的大聲公(手提擴音機)傳出。她的聲音對著執政者、警察、軍隊等國家機器,也向著前來支持的民眾、隊友。仔細去聽她這時的聲音包括歌聲,更脫離學生歌手階段時的婉轉,直接又開闊的聲線更接近搖滾樂歌手的聲音質地。此時期收錄在《壓不扁的玫瑰》(1983)、《大地是我的母親》(1985)的歌曲,人聲的表現比前一時期的聲線略低,有時唱到轉音情緒較飽滿處以刻意的「破音」表現,聲音質地裡蘊含著衝撞社會的氣氛。主要的伴奏樂器還是民謠吉他、鋼琴和電子樂器效果,但是她此時刷奏的吉他和弦之速度與手勁更接近民謠搖滾,且歌曲的節奏除了某些歌的風格並不適宜改變,其他以前也唱的歌很明顯地多了速度感。
《壓不扁的玫瑰》(1983)與《大地是我的母親》(1985)基本上延續之前專輯收錄國台語民謠、李雙澤等人作品的習慣,也收錄了楊祖珺的八○年代創作歌曲,其包括改編他人的歌與詩作。這兩張專輯因基於「保護作用」,當時專輯裡的文字資料並未列上參與製作的相關工作人員。《壓不扁的玫瑰》(1983)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採用了兩首羅大佑的歌曲之外,第一首歌選唱流傳於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的抗日救國歌曲〈賣花詞〉(1939),其他包括為了政治受難人和海外黑名單而傳唱的歌謠〈心肝兒〉。楊祖珺個人的創作曲則為婚前所寫的以描寫「理想主義者的心境與歷程」的〈累了嗎〉,與改編歌詞唱的〈台灣之乎者也〉。後者的歌詞猶如當時社會氛圍的寫實縮影,楊祖珺採用了原唱羅大佑半念半唱的方式表現:「雜誌查禁之/言論自由乎/所謂報禁者/強詞奪理也/李師科槍斃之/陳文成跳樓乎/所謂跳水者/王迎先是也」。
現在看來,《壓不扁的玫瑰》(1983)之曲目安排也別有意味。錄音帶A面由:1949年之前流傳的抗日歌〈賣花〉(A1)、1979年高信疆寫詞的愛國歌曲〈心中有一首歌〉(A3)、楊逵所寫的詞〈愚公移山〉(A4)、羅大佑創作「致中南半島難民」(實為描寫中美斷交之際台灣社會內外處境)與吳濁流抗日小說同名的〈亞細亞的孤兒〉(A5)、梁景峯向吳濁流致敬的〈老鼓手〉(A6)等歌組成。而楊祖珺的「壓不扁的玫瑰」競選宣言就放在當中(A2),似別有用意的將參選的動力與國共分斷前後的抗日、反帝歷史至「今日台灣」之抵抗強權的知識份子精神聯繫起來。錄音帶B面由:〈累了嗎〉(B1)、〈少年中國〉(B2)、〈心肝兒〉(B3)、〈美麗島〉(B4)、〈台灣之乎者也〉(B5)、〈我們都是歌手〉(B6)等歌組成。似是串聯各首歌曲原創者的「理想主義者」心境與對原歌者的致意,但是採用更接近八○年代議題意象的演唱方式和敘事安排。其中〈心肝兒〉則透露國共分斷後各階段的政治犯、異議者再連結於「當下」歷史的問題關懷。最後由〈我們都是歌手〉作為尾聲,蘊含鼓舞大家一起前進、合作的力量。
《大地是我的母親》(1985)專輯標題即透露濃厚的環保意識,之中的兩首新歌為楊祖珺與《前進》系友人蔡式淵合作諷刺食安和核安問題的〈超級倒霉小市民〉(A1),以及她所填詞關懷自然環境的〈大地是我的母親〉(B1)。當中收錄了另一批之前沒錄過的台灣民謠:〈思念故鄉〉(A4)、〈收酒矸〉(A6)、〈百家春〉(B2)。其他尚有改編自蔣勳詩作的〈我在橋頭等你〉(A3;原詩〈我在橋頭送你:寫給TS〉),以及也是沒錄過的〈綠島小夜曲〉(A5)、〈藍與黑〉(B4)。這張專輯在曲目的安排上沒有像前兩張較有敘事性,但是兩首突顯環境意識的新歌已加強專輯主題。然而,幾首遙向過往政治社會運動致意(1979年橋頭事件),以及呼應五○年代以來各階段政治犯及其親屬感受的歌謠:〈心肝兒〉(A2)、〈我在橋頭等你〉(A3)、〈思念故鄉〉(A4)、〈綠島小夜曲〉(A5)等,則又延續她此階段所關心的群體與問題。而以往與〈美麗島〉一起收錄的〈少年中國〉,這次只收錄了前者,為民進黨成立前後,越來越糾葛的「中國結」與「台灣結」之爭的本土意識偏向埋下伏筆。
本節至此已大致回顧此階段楊祖珺擔任製作、演唱的三捲黨外錄音帶的歌曲和延伸的意義。不難解讀出,其將歌曲、民謠作為銜接過去歷史和當代的意圖,也透過收集/錄製民謠和禁歌以尋索和安置台灣戰後史政治禁忌的一頁,亦深化了當代「民歌」的意義。
此階段的楊祖珺新學到的、也時常唱的歌謠還包括:〈坐牢算什麼〉與〈安息歌〉,這兩首卻未曾收錄在她的黨外錄音帶。這兩首歌都是1984年由在綠島服刑期滿十年之後,回台時先暫住她家的政治犯史庭輝教她的,而史庭輝又是學自1950年因「麻豆案」入白色恐怖監牢至1984年才出獄的左翼政治犯林書揚。〈坐牢算什麼〉的歌詞言簡意賅:「坐牢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傳唱於「長期以來國民黨監獄中進步青年」。楊祖珺學得了這首歌之後,時常在「老同學」聚會演唱,也在黨外運動集會、街頭抗爭與警方對峙時演唱以鼓舞民眾。〈安息歌〉是史庭輝帶著廣東國語腔調拉著胡琴教給楊祖珺的,這首歌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於監牢裡為了即將接受死刑的「同志」而唱的歌曲。之後,楊祖珺曾在楊逵的告別式(1985年3月)領唱此歌,也在往後與許多老同學相聚的場合一起唱著這首歌。然而,在1989年6月之前,她已在1988年1月隨解嚴前已推動數月的「外省人返鄉探親」運動第一個返鄉探親團「回大陸」時,在北京開了兩場民歌演唱會。此時已是後蔣經國時代初期,而楊祖珺是剛成立不久的民進黨的中執委。
回想這段將歌聲交給無數黨外政治活動、向著群眾的時期,楊祖珺曾感到矛盾與自責,在1986年前後即已不大受邀演唱,只因為綁束著「喪失了音樂的痛楚」。她在1992年出版的自傳曾提到:
黨外群眾運動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再加上經濟困窘、條件缺乏,藝術家進入黨外就只有等著餓死。在這樣的環境中推廣民歌,在音樂的對待、認識的要求上當然不高。
然而,我對音樂是有期待的!雖然它應該去鼓勵頹喪的、安慰受傷的心靈;它同時也應該在音樂專業上,有一定的水準。然而,群眾性、尤其是政治性的場合,要符合這些條件實在不容易。
唱啊唱的!我對自己在音樂工作上的墮落,往往令自己退縮不前,甚至有點不敢面對音樂了!
如果能時光倒回進行統計,不知道究竟能統計出楊祖珺在黨外時期中唱了幾次歌,以及場景和狀態為何。回頭在「綠色小組」的紀錄影片資料庫查詢,時常可見不管是什麼場合,她背著吉他或徒手或邊抱著兒子就唱起歌來。她的歌聲不是從什麼演唱會專業舞台擴音配置傳出來,也不像知名歌手、搖滾樂團們有著「靴腿」(bootleg)(盜版)現場錄音留存下來,她的黨外錄音帶究竟賣了多少捲也是個神秘數字。但是也說明了她唱的歌、寫的歌所交織的網絡,並不是通俗音樂文化工業視角下一般定義的歌手和樂迷、聽眾的關係。然而,這種從歷史反思學來的歌自己唱、從參與政治與社會所產生議題的歌自己創作、從他人刻骨銘心的苦難記憶學來的歌繼續唱……或製作、或錄下來、或自己(集資)出版,也許更是八○年代台灣通俗音樂產業朝更具現代商業規模的發展潮流中,所並行的一道地下/獨立音樂實作精神。
(未完……)
更多內容請見:《人間思想》第20期:馬克思主義在東亞
人間出版社網路書店
博客來
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