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1968】劉燁 | 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下)
1968在美國表現出不同於西歐的面貌。作為世界秩序的掌控者,美國的反抗運動最初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限度內,並沒有融入全世界的反抗潮流。是黑人解放鬥爭的參與者們,在實際的鬥爭中「走出」和「帶回」,使美國人重新認識到自身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從而使六十年代美國的反抗運動與全球關聯起來。
◎文章來源:保馬
◎文:劉燁
【保馬編按】1968在美國表現出不同於西歐的面貌。作為世界秩序的掌控者,美國的反抗運動最初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限度內,並沒有融入全世界的反抗潮流。是黑人解放鬥爭的參與者們,在實際的鬥爭中「走出」和「帶回」,使美國人重新認識到自身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從而使六十年代美國的反抗運動與全球關聯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黑人解放運動絕不等於「平權運動」或「民權運動」。另一方面,發生在美國的反抗運動再一次證明了,如果反抗脫離了現實的政治目的而僅僅滿足於一種「虛構的凱旋」,那麼這種反抗將只能耗盡自己的能量。換言之,必須反思人道主義在革命中發揮的影響。
◎上篇:【反思1968】劉燁 | 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上)
「帶回」是另一個美國在六十年代的重要意向,它表示在經驗上重新認識周邊世界及和自己的關係,由此形成對外部理論新的接納與回應。人們被迫認識到,美國不是一個光榮而正確地懸浮在地球上的國家,而是某個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心,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將痛苦和幸福來回輸送,造就統治和被統治的地形。「帶回」是一個與「出走」並列的概念,此兩者的共同作用才使得美國的六十年代與全球產生根本關聯。「帶回」不是一個模糊的意向,而是體現在實際的戰鬥策略中。他一方面牽涉到對美國以外的人民的理解,即世界面貌返照在美國內部,豐富了美國自身的定位與認識,由國境線、公民身份、立國神話和在世界體系中處於掠奪地位政治經濟結構共同合圍的世界觀至少在某幾個瞬間保持了開放,產生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可能;另一方面則是更具象的。這在反越戰運動中更明顯了。
如果說黑人解放鬥爭中抗暴的黑人領袖出走古巴、中國、越南和非洲,在觀念和邏輯上初步聯繫美國和革命中的世界,那麼越戰就更是美國主動闖入六十年代並將其升級的另一條線索。六十年代的傳媒技術使得越戰成為一場大規模的直播,而彩色攝影和電視的普及使得蒼翠的熱帶叢林和凝固汽油彈綻放出的琥珀色在螢幕面前帶來攝人心魄的反差。非對稱戰爭造就的大規模屠殺伴隨著美軍傷亡人數的急劇攀升,美國人意識到「我們的國家在遠方殺戮著成千上萬的人」。「在一個暴力的時代,看著你的國家在別國屠殺無辜的人民,如果什麼也不做,只繼續享受中產階級的舒適,這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越戰時期的著名照片。
越戰時期的著名照片。
瑪律科姆不早就說過嗎:
如果暴力在美國是錯誤的,那它在海外也應是錯誤的。如果保衛黑人男女老少的暴力的錯誤的,那麼美國強征我們到海外去暴力地保衛它也就是錯誤的。反之,如果美國有理由強征我們並教會我們學會暴力地保衛她,那麼你我就有理由不惜一切手段在這個國家裡保衛自己的人民。
美國對外暴力將在國內催生同等的反作用力。
一定程度上,越南之于美國如同更早的阿爾及利亞之於法國。越南戰爭成為冷戰中最大規模的熱戰,軍隊在海外的殘暴讓人們無法將國家的內外兩張面孔統一起來,人民難以忍受這分裂並開始走上街頭,政治的熱情燒得更旺了。越南不僅是美國的越南,也是全世界的越南。「帶回」的邏輯是「將戰爭帶回家」,即把戰爭的殘酷和不義以一種正義的報復方式帶回本土,讓美國不得不面對它在海外施行的一切殘暴。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報復帝國。再具體些,也是把自己看做世界革命中有相應位置和明確分工的一部分。第三世界進行著反抗帝國的鬥爭,而帝國內部的人應當策應第三世界的攻勢,對帝國進行內外夾擊。正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告訴羅伯特·威廉姆斯,現在是將戰線帶回到美帝國主義內部的時候了。這「帶回」使得第三世界在1968年前後驟然清晰且有力起來,得以在第一和第二世界中密集而具體的呈現。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間互為鏡像,人們在自己身上想像彼此、成就彼此。在革命的語境下,美國對越南的侵略產生了世界秩序的一種反轉,將弱小的越共和北越在全球的注視下加速塑造為格瓦拉式捨身鏖戰的英雄,胡志明也一躍而成世界舞臺的中心角色,他的名字無人不知。受壓迫的小國反而因此具備了巨大的道義能量,一個政治和經濟上處於邊緣位置的小國卻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把握了中心議題的主動權,攻勢淩厲,對強大的帝國主義毫不示弱。在某一刻,東風不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物質力量,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壓倒西風的勢頭。它用哲學的語言向世界指出,弱小能挑戰強大、邊緣能挑戰中心、卑賤能戰勝高貴、新的能挑戰舊的,沒有任何秩序是神聖不能顛覆的。霸權一旦形成,其本質是規定性和壓制性的,而異質力量最終能突破霸權對它的規範、收編或剿殺,改寫規矩,解放的潛質因之得以釋放。
 越戰期間,美國的反戰遊行。
越戰期間,美國的反戰遊行。第三世界的經驗與理論受到了認真對待。1968年由反戰學者(大多是高校學生及年輕教授)組成了亞洲關注學者委員會(發起者包括了日後各自領域的著名學者,如裴宜理、馬克·塞爾登、布魯斯·卡明斯等)。該委員會是「一種亞洲和西方學者間的溝通網路……一個發展反帝國主義研究的群體」。1971年夏,他們成為1949年後第一批走進中國的美國訪問團。他們考察了政治、經濟、教育、工廠、城市、公社、藝術等多個領域,也對周恩來做了4個小時的專訪。次年春,他們在美國出版了轟動一時的《中國!在人民共和國內部》(China! Inside People’s Republic)。其扉頁印著:
周恩來的話:
如你們所見,社會的轉變需要時間。近年來,毛主席已經注意到這一事實:美國正處於偉大風暴的前夜。而至於這風暴將怎樣發展,不是我們的——而是你們(指美國到訪者)的任務……
在當年第二批訪問團中就有百合的小兒子艾迪·河內山(Eddie Kuchiyama)。在人民大會堂的座談會上,周恩來問他,你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矛盾是什麼?艾迪後來寫到,「我緊張得快要尿褲子了」。他答,「是美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矛盾!」周恩來說「正確,聰明的年輕人」。
當然,將「帶回」執行的最激進的還屬越戰催生的多種反抗組織。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 WU)是一個舉國關注的武裝團體的典型。該組織屬於日漸激進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SDS主體是學生,但1966年持馬列毛主義的進步勞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也部分地加入了他們,並鼓勵他們掌握階級分析方法和反帝國主義的視角。1968年,在芝加哥召開的SDS全國大會上出現不同傾向,激進者最終在1969年夏秋間演變出的新的派系,即WU。其名稱源于鮑勃·狄倫的歌詞「你不需要一個氣象員也知道風往哪兒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氣象員們大多是白人大學生,領導者包括了1968年4月哥倫比亞大學佔領運動的核心人物馬克·魯德(Mark Rudd)。他們一方面希望能在革命激烈的洗禮中,滌去白人的「原罪」,實現真正的種族平等。另一方面,他們明顯對和平抗議在美國的前景感到絕望,他們相信既有體制對和平抗議所能帶來的改變已經達到極限,換句話說,體制對和平抗議已經免疫了。那麼,是時候直接砸碎體制了,暴力推翻美帝國主義的目標寫進了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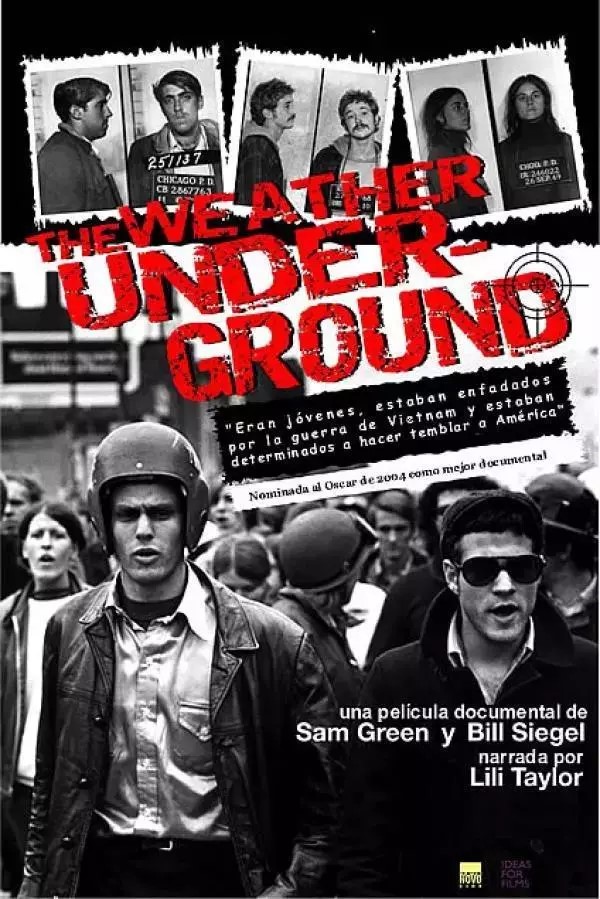 2002年的紀錄片《地下氣象台》的海報。
2002年的紀錄片《地下氣象台》的海報。1968是個眼花繚亂的頂點,是也個分水嶺——在這一點上,美國和歐洲幾乎同步。1968過後的時段並不能簡單地描述為左翼運動的退潮,而是一種分化。1968及以前,運動的參與者只需要有相對寬鬆模糊的認同便能結成同盟,時局尚不要求人們做出清晰的路線選擇和政治決斷。同時,資本主義體制的彈性和轉化能力對暴亂的容納也處於張力的最大限度。所謂1968就出現在這樣的瞬間。對待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態度各有差別,多方力量在團結、誤解和相互借力間交錯平衡,造就某種偶然且暫態的均勢。隨即局面將撐破,舊的矛盾隨之殞滅、資本主義處在新的階段裡,選項已經在世人面前攤開:既然已經濕了腳,那麼是在淺灘嬉戲,還是繼往深水處涉行?對無處不在的反抗者而言,他們需要回答是否要建立更嚴密的組織,往更艱巨的方向走去?是否應當將戲劇性地衝突轉化為看似瑣碎卻根本的對民眾的動員和團結?是否能克制絕對自由的幻覺而尋求個人與集體關係的辯證統一?在那個關頭,這些問題的答案將人們指向兩條路。
在這個節點過後,日本赤軍、義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法國直接行動小組,美國的黑人解放軍及氣象員等激進的暴力武裝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派今夜就改天換地的模樣(當然,在第三世界,更殘酷的武裝鬥爭早就如火如荼了)。而更多的未能邁出這一步的,又在超凡的宏偉儀式感的紓解下,做好了回過頭和日常和庸俗破鏡重圓的準備。朝著靈修、致幻劑、東方神秘藝術、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繼續發展。在這一脈絡裡,他們只選取革命的反常、激越、釋放而對革命要求的組織、紀律、集體、殘酷和漫長則無法認真面對。並放棄把握對這兩者間的辯證關係。資本主義塑造的人格與倫理觀依舊強大地起著作用,它使得革命行動始終無法擺脫既有的認識範疇,不能創設出新的矛盾(儘管在語言上行動者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這最終導致了反抗的空洞化也即政治的消亡。真正支配1968一代激情的核心是個體自由的世界觀。這些單純關注自我感受,認為解放乃是每個個體從壓抑的社會中直接掙脫而就可以達成了,激情反而使得嚴密的革命組織和機器更難造就了。從這一點說,六十年代在1968年那一刻已經發展成一個包含著自我瓦解的情形,那些使得革命的火焰驟起的因素在其後的某一時刻走向了反面,恰恰將革命釜底抽薪。造就1968的條件也註定要毀了它。
 1968年是個分水嶺。大部分「六八一代」在超凡的宏偉儀式感的紓解下,做好了回過頭和日常和庸俗破鏡重圓的準備。朝著靈修、致幻劑、東方神秘藝術、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繼續發展。
1968年是個分水嶺。大部分「六八一代」在超凡的宏偉儀式感的紓解下,做好了回過頭和日常和庸俗破鏡重圓的準備。朝著靈修、致幻劑、東方神秘藝術、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繼續發展。
地下氣象員就活動在這兩條路的糾葛中。
1970年5月21日清晨,KPFK廣播台接到自稱地下氣象員的來電。電話那頭是博納丁·多恩(Bernardine Dorhm)。此前,人們只知道她是芝加哥大學法律博士(J.D.)並協助過馬丁·路德·金工作。但此後,她被聯邦調查局列入最高通緝的十人名單。她當時在電話裡語氣淡然:
你好……下面我將宣讀《戰爭狀態聲明》。這是地下氣象員的第一次公報。全世界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人們,都期望著我們這些身處敵後戰略位置的年輕人的加入,和他們合力摧毀這個帝國……
成千上萬的抗議和遊行已無效……革命暴力正當其時……
現在,我們將採用越共的經典遊擊戰法和圖帕莫魯斯的城市遊擊戰法來對付這個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切·格瓦拉教導我們,「革命者當機動如大海中的魚兒」,而這個國家施于年輕人的異化和輕鄙已經造就了革命的汪洋大海。
……
如果你想找到我們,我們就在這兒:在每一個部落、公社、宿舍、農莊、軍營、聯排別墅:我們做著愛、嗑著藥、裝著槍。
……
在接下來的14天裡,我們將攻擊美國非正義的機構或符號……在敵後作戰以解放人民。
他們的登臺首演是未經安排的:在紐約格林尼治村地下室研製炸彈時操作失誤發生爆炸,三名成員和房屋一同化為灰燼。接下來的數年中他們用炸彈襲擊了紐約警察局總部、美洲銀行、三藩市普勒西迪奧軍事基地、哈佛大學、國會大廈。襲擊也儘量挑選特定時刻:抗議入侵老撾、回應阿提卡(Attica)監獄暴動、紀念古巴革命等。
氣象員們表達想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的願望。如Mark Rudd多年後回憶,「我們不斷地滌清自己身上的小資產階級成分,而希望像共產主義幹部那樣要求自己」。在暴力活動5年後的1974年,氣象員們發行了他們的政治宣言《燎原之火: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治》(Prairie Fire: 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Anti-imperialism)。在前言的結尾處寫著:
「燎原之火」基於這樣的信念,即革命的任務就是製造革命。這並不抽象。它意味著革命者必須深切地忠誠于未來的人性,運用我們有限的知識和經驗來理解瞬息萬變的局面、組織群眾和人民進行戰鬥。它意味著鬥爭、風險、艱辛和逆境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唯一的不變是永恆的變化,唯一的可能性是不成功便成仁(victory or death)。
儘管如此,氣象員,即這群白人學生的做法帶著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點與當時西方眾多類似組織非常相似。似乎群眾只是如符咒般想像中的力量,只需要掛在嘴邊就行。世界左翼運動的歷史輕易地反顯出氣象員們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無論怎樣將自己置於危險乃至犧牲的境地,他們都未能掌握物質力量從而轉變根本的社會結構。如同情境主義早年假設一般,他們創造的只是異質的景觀和符號。所出身的階級限制了他們對暴力鬥爭策略及其倫理觀的深刻理解,他們背叛其階級的行為失敗了。這正如1968年街上的學生和阿多諾論戰時,後者說,「思想中的烏托邦衝動越強,它就越不會把自己物件化為烏托邦(進一步的退化形式)並以此來代替烏托邦本身的實現。」儘管阿多諾不是一個革命者,但這句話在當時的情形中是有力的。諷刺的是,由於氣象員在每次爆炸前都會匿名通知那裡的人撤離以免傷人性命,氣象員們自首或被捕後並沒有遭到美國司法部門的殘酷鎮壓。一句話,國家未判別他們為體制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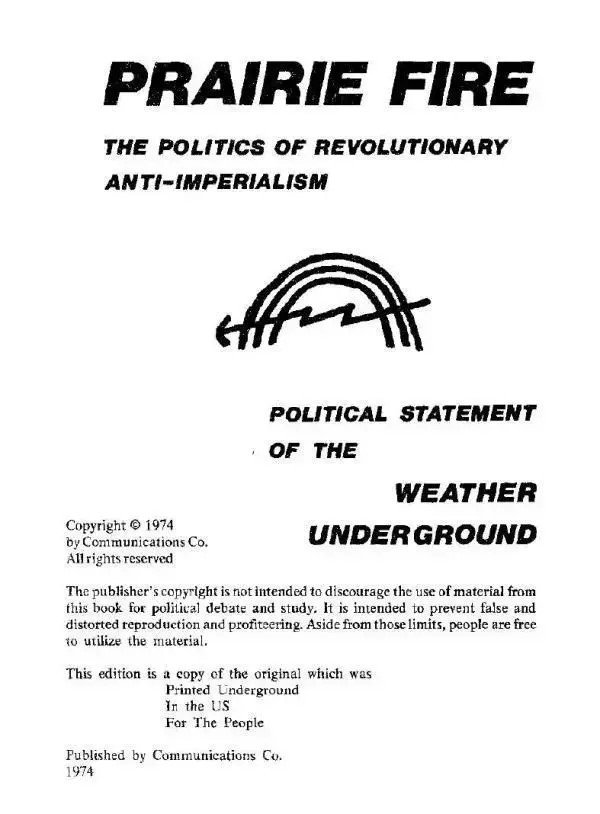 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 WU)的政治宣言小冊子:《燎原之火: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治》。
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 WU)的政治宣言小冊子:《燎原之火: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治》。
《燎原之火》指出了「燎原」的可能和必要性。武裝團體們正確信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時,卻發現一切都煙消雲散了,兩種看似矛盾卻根源如一的節奏就這樣出現了。美國和世界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海外的戰爭泥潭和的國內局勢動盪使得美國最終從越南戰場上收縮、停戰和撤軍,後來連西貢都徹底放棄了。反越戰的風潮不可避免地走低,1968的消散不遠了。
1975年春,美軍最後的力量終於撤離了越南。越共佔領西貢。越戰結束。
 1975年,《紐約時報》對美軍撤離越南的報導。
1975年,《紐約時報》對美軍撤離越南的報導。同年,百合長子比利在曼哈頓蹈海自盡,全家陷入悲痛,黑人解放軍團體致信弔唁。
1978年,祖魯·聶魯達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短暫任職後,他來到左翼旗幟院校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成為那兒的第一個黑人終身教授,此後他專注學術。
1980年,地下氣象員轉入地面,接受招安。和過去的一切道別。
1981年,黑人解放軍重要成員先後入獄,停止活動。
1982年,已被嚴重摧殘的黑豹黨停止活動。
到此為止,曾經劇烈地洗禮了美國的風暴已快看不出任何痕跡。在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的任期後,似乎雨過天晴了起來。福特總統(1974-1977)說「我們國家漫長的噩夢結束了」,他的四年任期也在對「六十年代狀態」的最終清場中耗盡(其後的卡特總統在就職典禮上稱「感謝前任為治癒我們的家園所作的一切」)。而真正阻斷六十年代延續性的是雷根總統(1981-1989)——唐納德·特朗普的偶像。雷根帶領美國重整「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再塑帝國金身。新自由主義下的帝國及其世界都變了,無需出走哪裡,也不必帶回什麼。
至於風暴的遺產,始終處於去政治化的處理中。其一部分轉化為青春、衝動和荷爾蒙的故事,將政治抽離具體的語境而將其視為一種「自然」現象、一種曾有著弑父衝動卻最終與父輩達成諒解的成年禮;另一部分則滋養著後現代的政治觀,成為今日認同政治(indentity politics)的重要思想基礎。不試圖對政治關係做根本的把握,反而刻舟求劍般地按照性別、種族、權屬等既定範疇區分著人群。它無處不在地談論著政治(以至於「XXX的政治」成為一種通行的句式),卻又在任何談論政治的地方阻礙它的到來。而六十年代真正危險的、卻也孕育著新生事物、帶有開創新局面潛質的特質還面目不清地埋在土裡,期待著我們的識別和重新創造。
(全文完)
【反思1968】劉燁 | 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上)
【反思1968】劉燁 | 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下)
【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兩岸從過去的隔絕對峙,逐漸走向和平往來,然而兩岸資訊因傳播媒介、傳播文化等差異,讓兩岸社會的資訊並不如想像中流通。犇報「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將微信上新奇有趣的公眾號資訊,以轉載的方式分享給台灣民眾,有興趣的朋友可關注相關公眾號,持續追蹤最新資訊。
◎文章轉載:【反思1968】劉燁 | 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
◎文章來源:保馬
◎文章出處:澎湃思想市場
【延伸閱讀】
‧ 【犇報社評】天佑美國,讓世界遠離種族主義的瘋狂和野蠻
‧「自由作為空氣」,但「我不能呼吸」!
‧ 為什麼美國黑人被員警打死事件經常發生?種族歧視在美國是怎樣的?
‧ 美國10萬生命隕落,政治霸淩科學的惡果
‧ 美籍韓裔作家:「為什麼我不再澄清自己不是中國人」
‧ 拒斥反中國,捍衛國際團結
‧ 中國人權研究會:美國種族歧視問題 凸顯「美式人權」虛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