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在理想的挫折面前——生命晚景中的尉天驄、劉大任、陳映真(上)
尉天驄、劉大任、陳映真是戰後臺灣重要的知識份子,早年他們因共同的左翼理想結下生死友誼,但理想受挫後,不同的人生價值和態度選擇,使他們走向了殊途異路。圍繞他們生命晚景中的表現和文字,本文試圖尋繹他們對待挫折和理想的不同態度,並勾勒出他們之間複雜的精神關聯和圖譜,呈現出理想主義時代終結對一代左翼知識份子心靈的衝撞。而他們或轉向,或遊移,或堅守的不同精神姿態,也發人深思。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8期,經作者授權轉載,分為上下兩篇,本篇為上篇。
◎作者: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8期,經作者授權轉載。
 從左而右分別為:陳映真、劉大任、尉天驄。
從左而右分別為:陳映真、劉大任、尉天驄。引言
20世紀左翼知識份子心靈史,可以說濃縮和象徵了人類理想張揚與受挫的全部歷史。知識份子的社會理想聯繫著人類悠久而普遍的烏托邦衝動,但是20世紀下半葉,伴隨著世界左翼運動受挫興起的反烏托邦思潮,卻是對人類擁有「更好的未來」的期望的嘲弄與取消。它的興起和發生,源於知識份子對歷史和現實「具體情境」的反思,但同樣身在當下具體情境的人們——比如處於民族歷史與現實語境的當代中國人——卻自有對這「具體情境」的判斷。歷史如何發展,知識份子該如何選擇,成為我們雖一再「告別」,卻始終無法擺脫的宿命般的「宏大命題」。它寓身於我們民族和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中,寓身於我們個人的生命史中,在理想的追尋、滿足與受挫中,向我們提出質詢。
在臺灣戰後以來的歷史中,尉天驄、劉大任和陳映真三人,都是生逢動亂又親歷了中國從落後到發展的一代臺灣知識份子。在風雨如磐的五十多年前的臺灣,他們因為壓抑,更因為壓抑之下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在陳映真生死交關的1968年,尉天驄、劉大任都曾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然而,這種由青春理想、生死考驗結下的友誼,後來卻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風煙中淡化、風散。這一切,始於與世界性共產主義運動受挫有關的理想幻滅——當早年的理想遭遇挫折後,他們開始尋求新的、不同的自處之道:轉向、彷徨,抑或堅守。這形成了他們此後不同精神趨向的人生與寫作,這是他們理想幻滅後不同心路歷程的照影。它們顯現著精神的交叉、衝突、往復,彰顯著「傷痕」與對「傷痕」的抗拒。
一、尉天驄:告別與轉向
《回首我們的時代》(後文簡稱《回首》)是臺灣學者尉天驄回憶舊人舊事的一部紀實性散文作品,其中《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後文簡稱《理想主義者》)一節記敘的是陳映真。裡面寫到2006年陳映真離開臺灣赴大陸前,他們的一次聚會:
那是二〇〇六年六月,他(筆者注:陳映真)要前往北京擔任人民大學的講座教授,行前邀我和黃春明、尤彌夫婦在臺北福華飯店的咖啡座小聚。那時,由於台海兩地的交往已經非常普遍,因此我們便像平日一樣只閒談著彼此間的家常瑣事,並沒有多少離別的情緒。但是,談話之間他忽然壓抑不住地說:「這些年來,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批評得體無完膚,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的莊嚴的意義的。」我聽了,只「哦!哦!」地作了平淡的回應。春明則張著兩隻眼睛,不作一語。於是這回談話就變成了他個人的獨語,那麼寂寞,那麼單調。春明知道我對文革很有意見,所以在映真去洗手間的時候,問我:「你怎麼對他說的話沒有反應?」我說:「都是什麼時候了,還要辯論這類問題!大頭(筆者注:陳映真的外號)的想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辯,爭論起來徒傷感情。」我們與映真夫婦的離別,便是在這樣的場景中過去了。注1

在尉天驄的這段敘述中,儘管有一種憶舊常有的感傷,但也明顯讓人感到他和陳之間有一種精神上的罅隙。熟悉臺灣文學者都知道,尉和陳有著非同一般的交誼:1959年到1961年間,包括處女作《麵攤》在內的陳映真最早的一批小說,都是刊於尉天驄主編的《筆匯》雜誌;1968年陳映真入獄時,尉天驄曾奮不顧身為其寫下辯護文字(後以《一個作家的迷失與成長》為題收於1988年人間出版社《陳映真作品集》第14卷);在陳映真囚於綠島的1973年8月,尉天驄冒著風險把其舊作《某一個日午》發表在剛創刊的《文季》第1期(署名「史濟民」);而到了1970年代著名的「鄉土文學論戰」,他們又勠力同心、共渡難關。僅上述事例便給我們「締造」了一個他們是朋友,且是志同道合、生死與共的朋友的印象。但《理想主義者》所敘的這個場景,卻顛覆了我們的印象。當尉天驄描述著陳映真「那麼寂寞,那麼單調」時,他眼裡的陳映真分明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人:孤獨、固執、寂寞。這裡流露的是一種明確的不認同,甚至厭煩。

朋友盡可以觀點不同,卻可以互相尊重。但厭煩,似乎排除了尊重的可能。尉天驄寫作這部作品時,陳映真已中風,所以我們看不到他的回應。而在這篇文字之前,我們也沒有發現他們有罅隙的證明,所以無法確定,尉天驄的厭煩起於何時。不過至少在1988年,他們還沒有任何問題。當時,人間出版社出版十四卷本《陳映真作品集》,第九卷收錄了尉天驄的《三十年來的夥伴,三十年來的探索》作為序文,尉天驄在文中回憶了陳映真1968年入獄時他營救的努力,以及陳入獄後為其發表「遺」作諸事,並以「三十年來,映真和我一步步往前走……讓我們再戰鬥二十年」為寄語,表達共勉之心。注2而在第14卷自序《總是難忘》中,陳映真似是作為回應,深情寫道:「畏友尉天驄寫的《一個作家的迷失與成長》,也許是評述我的小說的最早的文章。這篇評述,是就我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所做小說的內容,以存證文件的形式,直訴於當時的軍法處,證明我不可能是一個涉嫌『叛亂』的人。距今足足二十年的當時,為一個因政治原因被拘捕的朋友公開申辯的高度政治和身家破滅的危險性,是今天動輒上街『拉白布條』示威抗議的時代所無從想像的。」注3可以看到,當時在尉天驄眼裡,他和陳映真還是「我們」,而2011年,他眼裡的陳映真已咫尺天涯。

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在陳映真一方,我們找不到罅隙的證明,而從尉天驄的描述來看,陳映真當時對尉天驄的「厭煩」似乎也並不知情。也就是說,所謂「罅隙」很可能只是尉天驄單方面的。不管怎樣,目前的線索只能從尉天驄一方尋找。而循著《理想主義者》,倒也能尋到答案。
據此文所記,尉天驄(1935—2019)長陳映真兩歲,當年他們同是臺北成功中學的學生,尉高陳兩級。當時二人並無交集,但尉仍對各方面表現活躍的陳(擔任吉他社社長,常在學校壁報上發表作品)「有深刻的印象」。直到1959年尉接編《筆匯》雜誌,邀陳撰稿,二人才真正交往起來,從1959年到1961年,《筆匯》接連發表陳的《麵攤》《我的弟弟康雄》等11篇作品。
《筆匯》停辦後,陳映真加入《劇場》雜誌,至1965年退出。這期間尉天驄生病,陳則先是服兵役,後進入臺北某私立中學和藥廠工作,交際疏淡。尉天驄認為,也正是在此期間,陳開始發生變化。他認為,《筆匯》時期陳映真對社會的批判還只是「情緒上」,此時則已轉變為「理智上」,他甚至從《將軍族》看出,當時陳的理想主義「已到了非走到實踐的道路不可」的地步;而待到1966年《文學季刊》創刊,陳發表《唐倩的喜劇》《六月裡的玫瑰花》等,其精神轉向已不言自明。1966年大陸「文革」爆發,世界左翼運動洶湧,尉認為,這時的陳真正從「理智」走向「行動」:推動《文學季刊》改組,發表《最牢固的磐石》等……陳映真正式從「理想主義」走向「革命主義」。
這種「革命主義」的轉變,正是尉天驄不認同陳映真的開始。尉借用他和陳共同的朋友南方朔的話論道:理想主義轉變為革命主義「必然要經過一番靈魂的煎熬」,「懷抱烏托邦主義的人在人生態度上有著根本的信念,它的第一要義就是現世乃是一種墮落;『道德的人』被拋棄到了『不道德的世界』;如此一來,他便成為現世的否定者,否定別人,也否定自己……如此一來,個人對人世事物的真實感受便漸漸為某種意識形態所牽引,所控制」。為證明這一點,尉天驄特意舉了陳映真當年和戀人分手一事為例,他說陳給出的理由是:「一個人要是一直沉醉在羅曼蒂克的夢裡,是什麼事也做不出來的。」此外,陳和崇尚個人主義的作家七等生爭論,指斥存在主義哲學為「狗窩裡的哲學」,談論大陸出版的《紅岩》《西行漫記》,等等。在尉天驄看來,此時陳「原有的理想主義便在他的生命裡一步步轉變成為蘇聯式的烏托邦」。
不過,在敘述到陳映真這一轉變時,尉插入了這樣一句話:「他的這種真實的轉變過程,我是要到他出獄後,才從他的自白中得知的。」注4這句話表面上看沒什麼破綻,但仔細辨別,卻耐人尋味。尉天驄說他是在陳的「自白」中才知道他思想變化,而結合《理想主義》前後文可知,這個「自白」指的是1993年陳映真署名「許南村」發表的《後街》。注5也就是說,尉天驄是在1990年代才知道了陳映真1960年代的思想變化。這也意味著,當1988年的尉高喊著「映真和我一步步往前走……讓我們再戰鬥二十年」時,他對陳的思想狀況是毫不知情的。從邏輯上看,這說得通,但問題是,從1964年至1993年,時隔三十年,這三十年間,陳映真因「組織聚讀馬列共產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而入獄;更在出獄後的1983—1987年發表了表達革命信念的小說《鈴鐺花》《山路》《趙南棟》(第一篇寫得比較隱晦,後兩篇寫於解嚴前後,所以對革命理想的表達已不再那麼諱莫如深);而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陳更是幾乎全力投入社會實踐(如創辦《人間》等),這些實踐顯然比文字更為顯豁地彰顯著陳的左翼理念。而與他屢有交集甚至深度介入其生命歷程的尉天驄,如果說在這三十年間竟對其精神信仰「毫不知情」,怎麼說都是有些讓人難以置信的。
這樣去推測的話,尉在敘述陳思想「左」傾時插入的那句話便有些有意洗白的嫌疑了。換句話說,當他回顧、批判陳思想「左」傾歷程時,他似乎也在努力抹去他在那個歷程中的痕跡,撇清他和那個他所批判的人的關係。通讀《理想主義》會發現,那種「抹去」「撇清」的痕跡從一開始便有了,尉開篇便談到當年他們那一代青年的理想主義追求,但語中流露的,卻盡是一種「年少無知」的口吻:
回想起來,陳映真和我,以及一些朋友在年輕的時代都可以算是具有理想的一群。由於彼此都遭遇過不少的戰亂,大家都期待著一個公正的、互相關愛的社會到來……我們這些人也說不上來是左派還是右派,但癡迷到了某種程度,有時也會……一廂情願地把自己塑造成流行的左派人物……幾十年過去了,整個世界都有了巨大的改變,在幾經折磨後,有的人夢醒了,有的人仍然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中……注6
當年是左派,而今卻成了「說不上來是左派還是右派」;當年聲稱要一起戰鬥,實際上也曾一起戰鬥,現在卻說是「一廂情願」追逐「流行」。看到這裡,再去分辨那「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中」的人是誰,「夢醒了」的人又是誰?一切似乎不言而喻。
說白了,這篇文字所表達的,其實就是一種精神轉向。在《回首》中,「轉向」還有其他體現。卷首是一篇題為「寂寞的時光與靈光」的序,作者是「文化台獨」的理論幹將、與陳映真曾數度論戰的陳芳明。在這篇序言中,陳芳明「贊賞有加」地談到了尉天驄晚年的變化:「時光回流到一九七〇年代,當他還在主編《文季》的時期,可以發現他抱著對峙與對抗的態度,毫不留情,嚴厲剖析現代主義作家的小說」,而今天的他「許多憤懣之氣逐漸收束起來」,「在他溫潤的文字裡,釋放出一種慈悲,截然不同於他年少時期的脾性」,「他的文字,經過時間的淘洗,讓許多雜質沉澱下來,浮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澄明清澈。沒有遭遇思想上的風暴,沒有經過情感上的過濾,就不可能使狂飆的語法與句式獲得升華」。與上述評價相對,陳芳明後面評價尉天驄的話則或暗或明指向陳映真——「對於臺灣這小小海島,他懷有無比的信心,永遠堅持民主改革的立場,不會因為早年閱讀過社會主義書籍,而幻想著烏托邦式的革命」;「其中最令人傷感的一篇文章,莫過於《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瑣記陳映真》……寫到最後一次見面,他委婉暗示,兩人之間的思想取向已經背道而馳……這是思想的分歧點,也是情感的斷裂點」。作為第三者的陳芳明的這些話,可以說進一步佐證、坐實了我們之前關於「罅隙」的推斷。而這佐證竟出自與陳映真有「十餘年的對峙」注7的陳芳明之口,難免不讓人有一種世事難測之感。
曾為「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主將的尉天驄,乃是戰後臺灣左翼,這是瞭解臺灣文學史的人的共識,但《回首》卻顛覆了這個印象。這裡的尉不僅批評陳,也在質疑著他們一代人的理想主義追求。在自序《書前的話》中有這樣一些句子:「記得不久之前,朋友間有一場聚會,其中有些人當年曾經是左派,也有人曾是右派;有人曾是統派,也有些人曾是獨派……老友相會總不免『偷閒學少年』那樣唱起年輕時唱過的歌來,不過多少平添了嘲諷的意味而已。」注8這裡盡是一種毀卻當年的語氣。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二、劉大任:受挫與反思
《回首》附錄了尉天驄和劉大任一篇題為「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的對談,對談圍繞劉大任的小說《遠方有風雷》(2010)展開,這是劉大任反思1970年代海外保釣運動的一部作品,主要涉及當時運動的組織形式——「小組」。劉大任認為,這種組織形式是中國左翼革命的「創造」,但它包含著「『一元論』的恐怖」,尉天驄則直接對其展開了激烈的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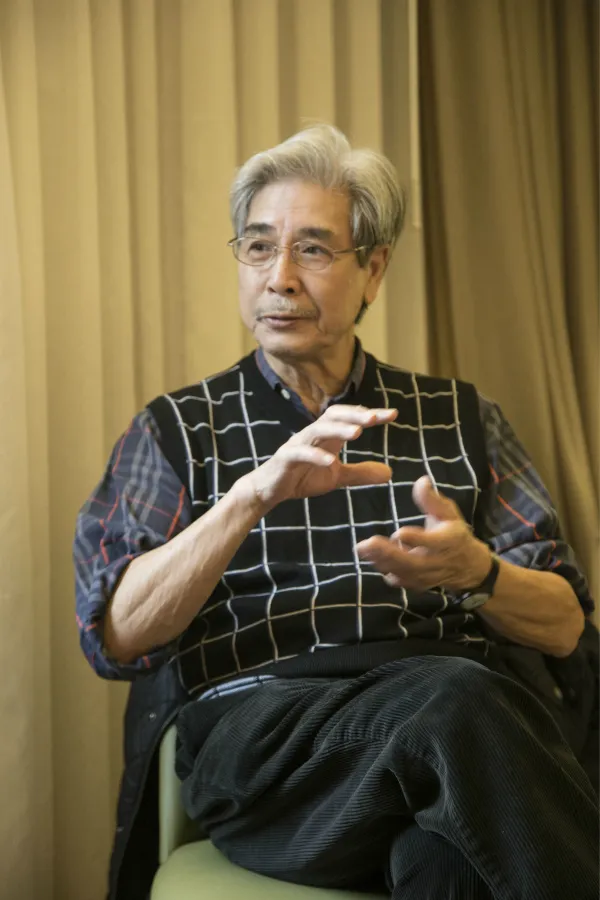
尉天驄的轉向、對陳映真的批評,是世界左翼運動受挫的結果。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認為,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標誌著時代精神的決定性轉變」,他說:「我們正在見證的不僅僅是左派的敗走麥城,而是它的轉變,也許是逆轉。」注9尉的表現——批判共產主義、否定青年時代的理想主義追求——恰恰是對雅各比這句話最好的「注解」。
但對於尉天驄的態度,劉大任卻不盡認同。劉是陳映真、尉天驄青年時代的舊友,生於1939年,三人都是臺灣戰後成長的一代,但與在臺灣出生長大的陳不同,劉和尉都是1949年前後遷台的外省人——尉原籍江蘇碭山(今屬安徽),十三歲跟隨姑父任卓宣、姑母尉素秋注10抵台,後畢業、任教於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劉原籍江西永新,1948年隨全家赴台,畢業於臺灣大學哲學系,1966年赴美就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所,1971年投入保釣運動,1972年入聯合國秘書處工作至退休。劉早年和陳一起踏上文壇,發表過《大落袋》《落日照大旗》等,1985年發表《浮游群落》,近年發表有《遠方有風雷》《當下四重奏》(2016)等,王德威稱劉為「海外左翼現代主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保衛釣魚島運動的關鍵人物」。注11陳映真去世後,劉大任寫有悼念文章《那個時代,這個時代》。據文章所記,他和陳初識於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但至1962年劉加入《劇場》雜誌,才和時為雜誌同仁的陳交往密切起來,尤其是此後兩年,劉大任在海外讀到大量為臺灣禁絕的左翼書籍而思想「左」傾,於是便和同樣「左」傾的陳映真一同退出現代主義風格的《劇場》,轉而與尉天驄合作,創辦《文學季刊》。注12
後來陳映真開始組織地下讀書會,而劉大任和他相熟後也被介紹加入,但因為臨近出國劉只參加了一次,不料就是這一次密會,也讓他成為了陳映真案(「民主臺灣聯盟」案)的涉案人員。注13三十多年後,劉大任仍心有餘悸地說:「在一九六八年後那幾年,我相信自己的文學和政治觀點基本上與陳映真相近或一致,如果他可以因此下獄受刑,我便沒有任何理由不受到同樣的待遇。我的僥倖只在於某些因緣剛好出了國,逃出了製造白色恐怖的那個國家機器的掌控範圍。」注14
1970年代初,身在柏克萊的劉大任投入保釣運動(為此放棄博士學位、十七年無法回台),作為骨幹的他後來還受到周恩來總理邀請於1974年到訪大陸,不過,似乎正是這次訪問,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1974年我去大陸,發現當時……毛病大得不得了,回美後,我做了一場報告,最後一句總結惹禍上身,被戴上『修正主義者』的帽子,這也是我決定申請到非洲去的原因之一。我慢慢退出『保釣』的開會和活動,開始考慮安身立命的問題,最後決定回歸寫作。」注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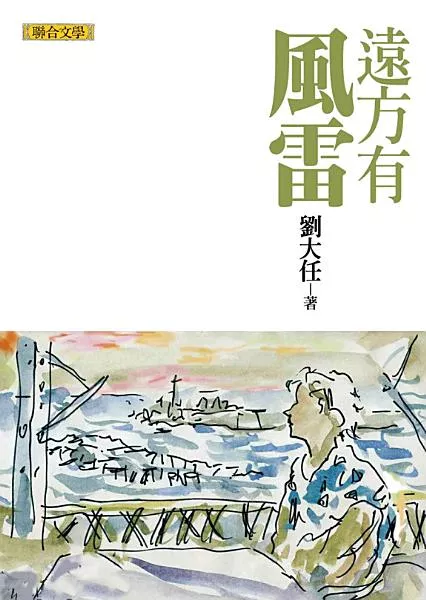
《遠方有風雷》所表達的便是對保釣運動的反思。但這種反思卻與尉的批判和否定不同,這不同體現在劉對待陳映真的態度上——當尉拿劉和陳做對比,認為保釣後坦承理想受挫的劉比「文革」後仍「執迷不悟」的陳更真誠時,劉認為,自己和陳不同只是人生定位不同罷了——
我自己對給自己的定位,大概和陳映真給他自己的定位不太一樣。陳映真是要改造世界的,而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知識份子……
基於這種理解,他對陳映真還有一種更深在的敬重:
我瞭解陳映真晚年心境的苦悶,那種熱情還在但卻無能為力的感覺是很痛苦的……我們雖然是那麼好的朋友,從二十幾歲開始交往到現在,但每個人的命運卻不一樣,映真是更不幸一點,我相信如果我沒有出國的話,也許沒有映真那麼堅強,可能活不過牢獄之災,就會被摧毀掉了。注16
其實,劉大任出國後,還一度與陳映真保持通信,甚至陳受邀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也是源於劉向、聶華苓、保羅·安格爾(Paul Angle)推薦,而陳被捕後,劉亦四方奔走,並通過保羅·安格爾斡旋,使陳案在《紐約時報》等曝光。不過,這種患難與共的友誼在陳1975年出獄後卻出現了問題:
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們之間的友誼出現了裂痕。他的政治活動,我不參與。這個態度,跟我1976年在我服務的聯合國自願報名、前往非洲工作的態度是一致的。我決定退出一切政治和社會活動,想盡辦法要拾回因參與保釣運動而失去的文學細胞。1987年臺灣解嚴以前,他是前政治犯,我在黑名單上,彼此無法聯繫。我也曾通過曲曲折折的管道,傳遞資訊,想說服他回到他的文學創作,得到的回應是:你太灰色,太沒出息了。
這個論斷,阻絕了我們之間任何恢復誠懇交往的可能性。注17
二人友誼出問題的細節我們無從詳查,但從上面的話中可以看出,對文學和政治等問題看法不同是主要原因。劉大任說1976年之後他「決定退出一切政治和社會活動」,顯然是和他參加保釣運動受挫有關。那麼,劉當年參加的保釣運動究竟有什麼問題?
《遠方有風雷》包含著答案。小說主人公叫雷霆,作品則以「我」講述父親雷霆和母親參加保釣運動的往事構成全篇。雷霆早年在南京便是「學運小組」成員,遷台後也曾因參加地下讀書會被捕,留美後他又攜妻子投入保釣,然而運動高潮過後,妻子卻突帶幼子返台,保釣亦陷入低潮。整個小說細緻而微地呈現了當時保釣運動的問題。這問題首先是保釣派內部的複雜性。比如學生群體構成複雜:既有臺灣留學生,又有港澳留學生;有的是外省人出身,有的則是臺灣本地人。成員家庭情況、身份、處境的差異導致革命態度、行動差異,比如港澳學生就比臺灣學生要激進,而臺灣學生又因出身、政治立場不同而有左、右、獨、統之分,加上國民黨官方威脅、分化、破壞,這就使得運動從一開始便遭受各種威脅。
另外,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小組」工作方式本身。這一點主要通過母親的眼睛呈現:第一件讓母親感到有問題的事是「小組」處理小吳和阿貞的離婚問題,阿貞和小吳是本省人、外省人通婚,因婚後無子,以及原先並不知情的「家仇」(阿貞父親作為指揮官處決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的小吳父親),這使得他們決定離婚,並提請小組決斷,「小組」先是開會討論,並以「婚姻存續必須以是否有利於工作為前提」說服,接著用投票表決的方式「挽回」了他們的婚姻。那次會議,第一次讓母親「覺得怪怪的」。而等到「送子事件」發生,母親則成了直接的受害者——當時保釣陷入低潮,為了再次挽救小吳的婚姻,雷霆在不和妻子商議的情況下宣佈要將她腹中的孩子送給小吳夫婦,這直接導致了母親脫逃。
在小說中,運動內外面臨的問題終於導致了雷霆的疲憊,而這樣的疲憊,是否也是當年劉大任心境的寫照?而它是否又是他後來被指責為「修正主義」的原因?總之,劉後來遠走非洲。然而,和從政治退回文學的劉不同,彼時剛出獄的陳映真卻因獄中「奇遇」,而決定走一條完全相反的路。於是,當劉大任勸陳映真「回到文學」時,陳則以「你太灰色」回應,陰差陽錯之間,便有了後來長時間的齟齬。
然而,對於各自的人生選擇,劉大任卻抱以寬容態度,他沒有像尉天驄那樣否定陳映真——不僅沒有否定,談到當年,他甚至認為陳遠比自己堅強:「我相信如果我沒有出國的話,也許沒有映真那麼堅強,可能活不過牢獄之災,就會被摧毀掉了。」言語中透著敬重。不過,這樣寬容理解的態度背後,似乎還隱約著其他東西。《遠方有風雷》雖寫到了對運動組織形式的反思,但劉卻從未否定過保釣運動本身。在被問到為參加保釣放棄博士學位、十七年無法回台是否後悔時,劉說:「唯一的遺憾是走得太急,紅旗打出去後就不可能回頭了……一開始就衝得太快,結果斷送了『保釣』這批人回臺灣的機會。這個運動後來在海外就風流雲散了。」意思也就是說,保釣方法有誤,但動機和目標卻沒有任何問題,不僅沒有問題,而且如果不是保釣派風流雲散,那場運動勢必會對臺灣和大陸關係格局產生決定性影響。注18也就是說,在左翼運動中受挫的劉大任,從未否定過左翼運動本身,從未否定過讓他置身運動的對祖國、民族的理想和情懷。
換句話說,在劉和陳身上,那當年促使他們共同走向文學、走向紅色中國、走向讀書會的可以稱為「理想」的東西一直都在。而這也成為他們後來複合的原因。劉大任2003年至2004年在臺北《壹週刊》發表了一系列回憶當年舊事的文字,裡面詳細記載了他在陳映真受難的日子裡的體驗:僥倖、擔憂、恐懼、噩夢注19……當時,身在臺北的陳映真讀到了這些文字,於是本已拒絕聯繫的他重新提筆,寫下了使他們重歸於好的一封信。
【下篇】:李勇|在理想的挫折面前——生命晚景中的尉天驄、劉大任、陳映真(下)
【注釋】
注1: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INK印刻文學2011年版,第218、218~219、252頁。
注2:尉天驄:《三十年來的夥伴,三十年來的探索》,《陳映真作品集》(9),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版。
注3: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14),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版。
注4:以上均參見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INK印刻文學2011年版,第239~245頁。
注5:原題為《陳映真的創作歷程:後街》,發表於臺灣《中國時報》1993年19—23日。
注6:同注1。
注7:陳芳明:《陳芳明悼陳映真:對這位可敬的論敵致上最高敬意》,http://culture.ifeng.com/a/20161123/50303005_0.shtml。
注8:尉天驄:《書前的話》,《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INK印刻文學2011年版。
注9:[美]拉塞爾·雅各比:《烏托邦之死——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姚建彬等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頁,前言、中譯本序頁。
注10:任卓宣(1896—1990),筆名葉青,四川南充人,國民黨政要、政論家。1920年代加入共產黨,曾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被捕後叛變,擔任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49年去臺灣。尉素秋(1908—2003),江蘇碭山人,中央大學文學系畢業、任教,1949年入台,任教於成功大學、中央大學等。
注11:王德威:《懸崖邊的樹——劉大任〈當下四重奏〉》,《當下四重奏》,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6年版。
注12:劉大任:《那個時代,這個時代》,深圳《晶報》2016年12月2日A21版。
注13:關於陳映真1968年入獄事件的具體情形,對當事人的影響,可參見李勇《陳映真入獄事件考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7期。
注14:劉大任:《噩夢》,《冬之物語》,臺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3頁。
注15:姚嘉為整理:《劉大任:我為中國人而寫》,《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
注16:尉天驄:《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INK印刻文學2011年版,第427頁。
注17:同注12。
注18:劉大任曾談道,當年保釣運動前後,臺灣旅美高級知識份子中有三個主要思潮,「人才最為薈萃而影響力最大的是保釣這一塊,其次是臺灣獨立運動的各派,而力量最弱的是保釣運動後期分割出來的……『革新保台派』」。後來主張愛國統一的保釣派回台路斷絕,在海外逐漸式微,臺灣今天的政治格局中便只剩下了「革新保台」逐漸發展來的「藍」和海外台獨發展來的「綠」。參見劉大任《拒見周恩來》,《晚晴》,臺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54~255頁。
注19:參見劉大任《冬之物語·第一輯白色恐怖》,臺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作者: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8期,經作者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1960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
‧ 陳映真的真,是什麼真
‧ 重尋陳映真先生的精神底蘊
‧ 為什麼讀陳映真?
‧ 高盧雞鳴 庚子生辰自壽兼懷大陳
